华人研究 | 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争点分析及类案检索
发布日期:2024-10-18 浏览次数:149
引言:
实务中经常会碰到,针对某一公司已经取得了胜诉判决,但是鉴于该公司并非一人有限公司,股东也履行了出资义务,此种情况下执行未果,往往会使得案件的办理陷入困境。那作为原告方,下一步还有什么措施可以采取呢?本文或许提供了部分思路,以供大家交流、讨论。
案件背景:
2021年7月,原告A公司与被告B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涉诉,后经某区人民法院审理并判决B公司向原告A公司支付货款300万元,申请强制执行未果后。A公司在其注册地作为原告再次提起诉讼,要求许某、王某、许某子、周某、王某因 对B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A公司本案提供的主要证据有2组,一份是证明各被告之间的亲属关系(其中,许某、王某系夫妻;许某子、周某系许某、王某的儿子、儿媳;王某因系独立个人),一份是银行流水,证明股东和B 公司之间存在大量往来交易,构成财产混同。
B公司的基本情况:B公司成立于2013年7月25日,现股东为许某、王某,注册资本50万元。其中许某子持股90%,认缴45万元;王某持股10%,认缴5万元。2019年1月18日,股东王某将其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周某。2020年6月5日,股东许某将其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给王某因。2021年6月23日,股东周某将其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合肥某商贸有限公司。截至目前,B公司股权情况为:王某因持股90%,合肥某商贸有限公司持股10%。
争点论证:
代理人代理本案主张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诉讼中,就案件的以下问题进行了法律论证和实证检验:
一、关于本案管辖法院的确定问题
本案,作为被告方要不要提管辖权异议。有两种观点:第一,原告住所地法院有管辖权;第二,应当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
法律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十四条:“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
第一种观点认为:本案本质上侵权责任纠纷,侵权结果的发生地也即原告住所地也有管辖权,提起管辖权异议大概率最终会被驳回;(参考最高院(2018)最高法民辖80号1、(2018)最高法民辖162号1)
第二种观点,应该有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在上海市一中院【(2019)沪01民辖终85号案】中认为:“若只是因原告承受了侵权结果,就可将其住所地视为侵权结果地,则几乎所有侵权案件权利人的损害总会反映到原告住所地,如此,有可能使侵权结果发生地“泛化”,等于是废除了被告住所地标准,会导致对被告管辖利益的重大损害。而侵权行为的管辖规则是在原告和被告之间实现管辖利益平衡,而非将所有案件都划归原告住所地管辖。故侵权结果发生地的界定应当以直接结果为标准作合理的限定。”本案中可以参照提出。
二、关于本案争议焦点——股东、董事、总经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各被告是否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
法律依据:《公司法》(2018年)第三条:“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第二十条:“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
(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
(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
(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
原告方认为:首先,在B公司经营期间,巨额资金向许某及股东王某、许某子个人账户转移,且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资金转移的实际交易用途,该行为明显属于转移公司资金、滥用股东有限责任和公司法人的独立地位,符合公司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混同的情形,而且导致了公司偿债能力明显降低,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许某、王某、许某子三被告应当对B公司的债务向原告承担连带责任。被告许某虽不是公司股东,但其配偶王某是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公司的款项大部分都是转给了许某个人账户,其夫妻二人系作为一个共同意识联络主体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对转移公司资金是明知的,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其次,B公司注册资本一直都是 50 万元,B公司及其股东在经营过程中,股东实际投入公司的资本数额与公司经营所已含的风险相比明显不匹配,被告许某子、周某、王某、王某因作为B公司的原股东及现股东利用较少资本从事力所不及的经营表明其没有从事公司经营的诚意,实质是恶意利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把风险转嫁给债权人。故对被告方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予以确认。
被告方观点:从本案的转款事实及时间来看。首先,本案系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许某自始至终不是B公司的股东,原告要求许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其次,股东承担有限责任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法律规定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着严格的规定,只有在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才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B公司确实是向许某子、王某个人转账,但是因B公司业务合作对象有大量的民营企业,要求B公司以个人名义代B公司付款,且也是支付到其他民营企业股东、法人个人或者指定的人员账户中,本案中原告也曾经大量接受许某的个人转账,该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许某子、王某在收到B公司的转款后,大部分又支付给许某,再由许某支付给B公司的供货商(少量可能直接支付给供货商)。B公司股东从未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尤其是王某,原告诉称的款项是发生在2019年至2021年期间,而在接受B公司转款期间(2015.1.16-2016.3.21),B公司与原告的款项均全部结清,不存在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
其次,许某、许某子、王某实际个人代B公司支付的货款远超过B公司支付给三位个人的款项,更不存在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
再次,关于本案抽逃出资的问题。B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均已实缴。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的规定,被告王某、许某子从未有过任何抽逃出资的行为,原告据此要求该二人对B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最后,关于要求被告王某、周某、王某因 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3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指的是董、监、高如有该类行为,应当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而不是向公司的债权人。且,本案中王某、周某、王某因从未有任何损害公司利益或者造成公司损失的行为,从原告提交的证据看,B也未给周某、王某因支付过任何款项,原告据此要求王某、周某、王某因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另,被告方也检索了相关案例,结合案例主要观点如下:1.如果B公司不能提供完整财务账册,证明未发生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存在混同,则可能要承担责任。尤其是之前已经把股权转让出去了,可能也要承担责任。最好是能说明全部的款项流向;2.B公司应该举证证明资金用途,否则要承担责任;3.B公司股东受让后对公司债务的形成如果没有过错,可以不用承担责任。反之,如果担任股东期间,B公司对原告不负有债务,且公司支付的款项可以说清楚其他用途,可以作为一点抗辩理由;4.本案现有证据未显示B公司与周某、王某因之间存在交易往来,不能证明二者之间存在财产混同以及隐匿、转移公司财产的行为,未能证实周某、王某因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了债务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可以不承担责任;从相关检索案例来看,大部分还是支持原告方的观点。
三、结语评析
本案历经管辖权异议,一审支持移送被告法院管辖,上诉后二审改判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再到实体一审、二审均支持原告诉讼请求。为我们今后办理公司类案诉讼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践经验积累,即在取得针对公司的胜诉判决而又难以执行的情况下,应该仔细梳理案涉公司的历史沿革和调取公司的账户交易明细,以此判断股东是否存在滥用股东有限责任的问题,以及要求非公司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相应的责任,往往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本案中,原告最终基本执行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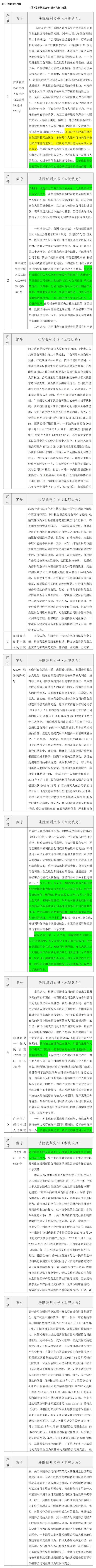
引 用:
1、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 》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未在法定期限内组成清算组开始清算,应对债权人主张的债权在造成公司财产损失减少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科伦比亚公司以朱卫东、李庆元为被告提起诉讼,属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之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十八条关于“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二十四条关于“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的规定,本案侵权结果发生地即科伦比亚公司住所地,和两名被告朱卫东、李庆元住所地,均可以作为确定案件管辖法院的连接点。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为科伦比亚公司住所地的法院,在先行受理本案的情况下,将本案移送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审理错误,应予纠正。
2、该条款现变更为现行《公司法》第二十一条
3、现变更为第一百八十八条
转载请注明文章来源

卢敏敏律师,法学硕士,民革党员,曾任安徽省破产管理人协会财产调查与审计评估业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合肥市破产管理人协会战略合作委员会委员。业务方向为公司治理、企业破产清算与重整、不良资产处置等民商事争议解决。自执业以来先后参与了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法律顾问团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安徽省分行法律顾问团队、安徽省司法厅法律顾问团队等,曾参与办理的池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被评为2020年度合肥市十大破产典型案例。



